跌宕自喜既可形容人,也可形容文(在“風(fēng)格即人”的意義上,二者又是統(tǒng)一的)。前者譬如有《明史·儒林傳》稱王畿“弱冠舉于鄉(xiāng),跌宕自喜”[23],錢泳《履園叢話》說饒介之“以元末亂隱居姑蘇,跌宕自喜”[24],等等,指向一種落拓不羈、任真率性、狂狷激切、爽朗活潑的性格,而馬雁就是這樣一個(gè)人。《俄羅斯的血液》:“有兩種俄羅斯人,偏執(zhí)、虔誠、矛盾的俄羅斯人,和熱情、自由、激烈的哥薩克”,這與其說總結(jié)了俄羅斯的民族性,不如說是馬雁的自況之語,她就是“兩種俄羅斯人”的混合。作為一種寫作觀念與文學(xué)風(fēng)格的跌宕自喜,在古典傳統(tǒng)中亦淵源有自。毛先舒以“跌宕自喜,不閑整栗”[25]概括李白(歌行)的詩風(fēng);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稱賀貽孫《水田居士文集》“所作皆跌宕自喜”,這既是稱贊賀貽孫“于古人文集之外,別有自得”,也是說他行文“特一氣揮寫,過于雄快”[26];錢基博《中國文學(xué)史》沿用了毛先舒的說法,指出陳子龍的七古“跌宕自喜,取藻于六朝四杰,而出入于太白昌谷”[27]。除了部分早期作品及報(bào)刊的約稿之作,馬雁的寫作不僅自覺地繼承了這一古老的風(fēng)格,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它的內(nèi)涵。
跌宕自喜的文學(xué)風(fēng)格與讀書大有干系,其得以形成的基礎(chǔ)性條件之一即博覽群書。馬雁認(rèn)同毛先舒對(duì)李白的評(píng)語,但她同時(shí)指出,在跌宕自喜的表象下,“是巨大的知識(shí)體系,因?yàn)槔畎住鍤q誦六甲,十歲觀百家’(《上安州裴長史書》),后人要學(xué)卻不肯下苦功夫,就成了粗率油滑”[28]。
跌宕自喜風(fēng)格的第一個(gè)特點(diǎn)是“快”(跌有疾行義,如跌蹏)。李白之所以贏得這一考語,是因“詞語迅快”、“思疾而語豪”,也就是“詩思和詩語之間的疾速”[29];賀貽孫也很快,所謂“特一氣揮寫,過于雄快”。而馬雁運(yùn)思造語同樣迅快如馬、雁一般,用范梈《木天禁語》里的話說,“突兀萬仞,不用過句,陡頓便說他事”[30]。《我是夢(mèng)中傳彩筆》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:
再來說買舊書,武宮正樹自然好,藤澤秀行也不壞,但還是武宮好,因?yàn)槊钟袣狻N乙蚕矚g大竹英雄,這個(gè)名字有點(diǎn)像古龍的小說,有《歡樂英雄》,還有個(gè)郭大路。但我不喜歡王動(dòng),因?yàn)樗粣垩嗥摺Q嗥哂悬c(diǎn)英倫范兒,因?yàn)榇蟾攀莻€(gè)平胸。燕子李三,我也喜歡,因?yàn)楹孟駮?huì)飛的樣子。拼命三郎就不好了,但《阿飛正傳》不錯(cuò),要電影才不錯(cuò),小說還是不行的,因?yàn)榘w太笨。因?yàn)樗谋浚B帶林仙兒也顯得不聰明了,因?yàn)榱窒蓛旱牟粔蚵斆鳎B帶林詩音也不清麗了。我還喜歡木谷實(shí),因?yàn)樗哪竟鹊缊?chǎng)好像一個(gè)農(nóng)業(yè)合作社的樣子,再加上他雖然不笨,但和吳清源一比,就好像榆木腦袋了。既生瑜,何生亮?
一氣呵成的轉(zhuǎn)換——有賴于讀書之雜,最后由“林”轉(zhuǎn)至“木”,再由木谷道場(chǎng)之“谷”“場(chǎng)”想到農(nóng)業(yè)合作社,因木谷實(shí)之“木”“實(shí)”而及榆木腦袋,最妙的是由榆木之“榆”想到字形相像的“瑜”,因清源之透亮感聯(lián)想到“亮”,那句成語又恰好貼合了木谷實(shí)與吳清源的實(shí)力對(duì)比,這樣的疾思快語“好像會(huì)飛的樣子”,試問我們還能跟得上作者的文思嗎?
像李白一樣,馬雁也是因?yàn)榭於罢Z多猝然而成”:在快速的語流中,話語結(jié)構(gòu)有時(shí)并不完整,甚而故意有所省缺以避冗贅。不過這種“省字約文”由于語境的支持,并不會(huì)造成語義的欠缺,例如“你唱歌我聽吧”[31](“歌”后省略了“給”),“那句我喜歡的王勃”[32](末尾省去“的詩”),“其實(shí)公路也就和游樂園小火車一樣,在盤旋”[33](“火車”后略去“的軌道”),“那個(gè)老頭兩分錢看三本連環(huán)畫”[34](“老頭”后省“的攤”或“那兒”)。省缺也會(huì)帶來陌生化、詩意化的效果,《第一只小板凳》:“急匆匆聽到下樓聲”,這個(gè)“急匆匆”的句子既有省缺又有語序之跌宕,“正確”的表達(dá)應(yīng)該是“聽到急匆匆下樓的聲音”,但顯然有些慢;馬雁是個(gè)狂熱的愛花之人,下列句子也逗漏了這一點(diǎn),“初中的時(shí)候攢了一個(gè)星期的零花買了《米尼》”[35](“時(shí)候”后省略“用”,“零花”省“錢”),“我揀了臨河的小桌,要了一杯菊花”[36](“小桌”后省“坐下”,“菊花”省“茶”),這省缺就像“腰帶上別一朵梔子花”[37]的少女馬雁一樣,用“花”裝點(diǎn)了一個(gè)句子。
《讀詩與跌宕自喜》:“(李白)因?yàn)樘欤圆荒芙⑿碌捏w系,卻把前代的精彩都籠括到他身上來發(fā)出奇光異彩”;葛兆光的原話是,“李白……囊括了古代詩歌傳統(tǒng)……他的天才足以讓他左右采擷隨心所欲”[38]。而博覽群書、博采眾長的俊快的馬雁不也是如此嗎?
除了快,跌宕自喜更是指向一種自由的寫作境界(宕有流動(dòng)義,如皇甫謐《三都賦序》“流宕忘返”;而跌宕的主要涵義乃放縱不拘)。中國古典散文從莊子的“逍遙游”,蘇軾的“萬斛泉流”說,陸象山的“胸襟流出”說,到公安派的“獨(dú)抒性靈”,均揭示了自由精神乃是散文體裁的魂魄。西方的隨筆同樣如此,阿多諾指出這種不必屈從于外部權(quán)威、最少形式束縛的文體,比起其他體裁更能起到喚醒知識(shí)分子自由意志的作用。[39]而馬雁可以說將散文的這一核心特質(zhì)發(fā)揮到極致。
就詞法而言,她并不滿足于現(xiàn)有的語匯,也不會(huì)完全遵循詞語使用的陳規(guī)舊律,不僅如此,她甚至故意在語言中搗亂。描述身段妖嬈的綠度母時(shí),馬雁生造了“曲致”一詞[40];《我是夢(mèng)中傳彩筆》中,“我外婆還管打火機(jī)叫‘點(diǎn)火器’,我覺得也很好,因?yàn)榇蚧饳C(jī)顯得太有科技含量了,其實(shí)哪有那么多”;《杭州》為了不透露老胡的性別,以“它”相稱,而對(duì)于貓或熊貓,乃至包括一段文字在內(nèi)的萬物,馬雁卻要用“他們”或“她們”來指稱,因?yàn)椤皼]有一個(gè)事物的存在是毫無生命力的,所有的事物都具有天賦的神奇本性,當(dāng)他們相互作用時(shí),激發(fā)出巨大的能量”[41]。當(dāng)代散文作家,大多只能算是語言的熟練工而已,在駕輕就熟的操作中,他們對(duì)語言本身既無所謂追問,也無所謂挑戰(zhàn),更無所謂發(fā)明;而宣稱“發(fā)明詞語者,發(fā)明未來”的馬雁,一直致力于通過創(chuàng)造性的寫作,對(duì)字詞及其可能性有所實(shí)驗(yàn)、拓展,工具型表達(dá)符號(hào)由此獲得獨(dú)立而突出的審美價(jià)值。
在句法、篇法上,馬雁同樣秉持一種典型的無政府主義方法論,以活法、萬法、無法為法,形成了一種貌似雜亂無章的風(fēng)格,一種接近于“文”之字源義的“錯(cuò)畫”之美,散見于本書中的下列句子提示了這一點(diǎn):“東一句西一句的好。真有意思”[42];“雖然這前面一句好像沒什么邏輯好推演出來,但就這樣吧”;“想怎么寫就怎么寫……就是故意要亂寫”[43];“其實(shí)只是想啰嗦一下,東拉西扯,在這些方塊字中間忽然覺到一點(diǎn)趣味和情調(diào),彌漫其間——奇妙的事情”[44];“沒有什么任務(wù)局限的時(shí)候,我傾向于用東拉西扯的方式寫文章”[45]。“東一句西一句”、“沒什么邏輯”、“亂寫”、“東拉西扯”,這些方式成就了一種徳勒茲所說的“塊莖式文本”。這種“塊莖式文本”解除了根–樹結(jié)構(gòu)的中心化和層級(jí)化制約,自由流動(dòng),隨意伸展,旁逸斜出,意態(tài)橫放,不斷衍生差異,制造新的連綴和撒播;它反中心、反總體、反譜系、反僵化,強(qiáng)調(diào)文本的隨意性、流變性、多元性、偶發(fā)性、散逸性、異質(zhì)拼貼性,從而帶給我們強(qiáng)烈的跌宕和迅快、自由與意外之感。“最愛是《菟絲花》……二十年后知道菟絲子是補(bǔ)腎的藥。補(bǔ)腎和瓊瑤沒什么關(guān)系,但也東拉西扯上吧”,這就叫,“瓊瑤差點(diǎn)害死我”[46],因此活該被拉扯;《人生只若初相見》中,一段非常理論化的表述之后,馬雁來了一句“上面不是亂碼”;《我這個(gè)人,脾氣很不好》:“‘若非群玉山頭見,會(huì)向瑤臺(tái)月下逢’,真是肉麻得要死。是我,誰拿這樣詩給我,我都要說:‘你不要寫奇怪的詩給我,因?yàn)槲覀儧]有萍水相逢過’”,虧她想得出,用徐懷鈺“沒有萍水相逢”的流行歌,回絕李白“見”、“逢”的肉麻詩;《棲水》打錯(cuò)了字卻將錯(cuò)就錯(cuò)地一路寫了下去,“又像菠蘿或香蕉。剛才打菠蘿,打出了碧落。碧落真好,抽象得好……”。結(jié)尾我們見得多了,可馬雁還是能用她的“亂寫”拓展我們的結(jié)尾觀,使我們大開眼界。《〈閃靈〉不耽誤時(shí)間》最后寫道:“我寫到這會(huì)兒,覺得基本上嘮叨夠了,可以告一段落了,但是和《閃靈》好像沒什么聯(lián)系。不是沒有直接聯(lián)系,是一點(diǎn)聯(lián)系都沒有。這種事情是不多見的。”“形散而神不散”的教條可以休矣。再看《讀詩與跌宕自喜》的結(jié)尾:“所以本來想寫的一些話到這里就不打算寫了。”以及《雙去雙來君不見》的結(jié)尾:“做題目的‘雙去雙來君不見’是《長安古意》里的,我自由自在地想成是《站在高崗上》的真相。真相殘酷嗎?其實(shí)不見得,真相都有一點(diǎn)悲哀,這倒是的。有時(shí)候想得太多確實(shí)很倒人胃口,就像寫這個(gè)文章,就是隨便寫寫,可是因?yàn)橹橇Φ拖拢跃屠s雜地寫這寫那,寫到結(jié)尾了還結(jié)不了尾。”
在馬雁跌宕自喜的寫作中,一篇散文并非是在演繹或歸納中達(dá)成的一個(gè)封閉結(jié)構(gòu),而是意識(shí)的云轉(zhuǎn)飄曶(《一念》最有代表性,簡(jiǎn)直“一念三千”)。 她的散文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“忽然想到”、“乍想起”、“又想起”、“轉(zhuǎn)念一想”等語詞,更多時(shí)候則連這些提示語都沒有,直接呈現(xiàn)活躍思緒的跌宕變化。對(duì)此,馬雁喜愛的克爾凱戈?duì)栒J(rèn)為:一個(gè)關(guān)于存在的體系是不可能的,因?yàn)榇嬖谑浅竭壿嫷模亲兓脽o常和荒謬的,“存在既然不可能被思想,而存在的個(gè)人卻在思想,這意味著什么呢?這意味著,他只能是斷斷續(xù)續(xù)地思想,只能是忽前忽后地思想”[47];克爾凱戈?duì)栂矏鄣呐了箍杽t說:“我要在這里漫無順序地寫下我的思想,但也許并非是一種毫無計(jì)劃的混亂不堪;這才是真正的順序所在,它將永遠(yuǎn)以無順序的本身表明我的對(duì)象。”[48]也就是說,恰恰是未被某種剛性結(jié)構(gòu)或邏輯性統(tǒng)攝的思想、倏忽變化的思想,才是與存在同質(zhì)的真實(shí)思想、生機(jī)勃勃的自由思想。馬雁曾說:“古代漢語‘思想’一詞的所指本就包含‘自由’的意思,且是動(dòng)詞(例見曹植詩作),但糟糕的是現(xiàn)在它已經(jīng)喪失掉了這些,成為一個(gè)可怕的名詞枷鎖。”[49]她的寫作就是要將“思想”從“可怕的名詞枷鎖”中解放出來,使其回歸古老的內(nèi)涵。
關(guān)于龍口市
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這
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這
 龍口網(wǎng)
龍口網(wǎng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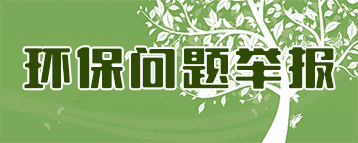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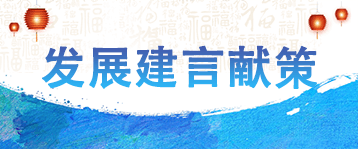



最新評(píng)論
厲害呀
最不靠譜,時(shí)間不準(zhǔn)時(shí)
16路車沒有上來
這幾個(gè)人還有臉亮?